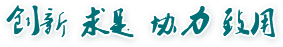【广州日报】珠峰:第三极生灵乐土
粤科学家团队调查珠峰野生动物,记录新物种193个
5月11日,广东省博物馆,讲座题目“活在世界之巅——珠峰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主讲人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恢复研发中心主任胡慧建展示了雪山下的野生动物图片,瞬间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3年前,胡慧建团队接下珠峰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本底调查项目,调查揭开了世界第三极生灵的新面目以及新记录193种物种。
珠峰这片秘境从来不缺乏目光,而保护区内的动物们无疑是主角,但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却称不上知根知底。珠峰保护区被誉为南北极外的第三极。它形成独特的立体气候,表现为“山顶四季雪,山下四季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它是一片少有人迹的净土,也是动物的乐土。
珠峰保护区分南北坡五大片区,“不同的地形决定不同的物种”,多样的地形造就了珠峰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知道有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恢复研发中心主任胡慧建说,有了认识,才会有后面的关心行动和希望。调查是可以更好地保护,从调研开始之初,保护也同步着,保护区的300多名潘得巴守护着保护区。
在天然的屏障和多方的努力下,世界之巅的动物们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生存成为可能。


棕额啄木鸟。李晶晶拍摄

高山兀鹫。彭波涌拍摄
“这是世界之巅的一片净土,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土,让我们珍惜她,呵护她!由此以敬畏之心爱护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生灵,让这个美丽的星球成为我们永久的家园。”广东省博物馆和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合作筹备《地球第三极的生灵——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展》,结束语如此写道。
雪豹偷吃“醉”血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珠峰保护区),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保护区,也被称为除南北极外的第三极,珠峰保护区是全球最为神秘、最奇特、最富多样性的自然保护区,吸引着众多中外科学工作者和旅游者。
事实上,早在1958年,珠峰保护区的科考就已开始,但并未真正揭示保护区野生动物的本底,还有许多漏网之鱼。
2010年10月,受珠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委托,执行“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项目,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开始了对保护区内陆生野生脊椎动物为期近3年的细致翔实的调查。
在大气环境和喜马拉雅山脉阻隔的双重作用下,保护区沿夏邦马峰-卓奥友峰-珠穆朗玛峰-马卡鲁峰一线分为南坡和北坡两大区域。北坡的藏南山原、宽谷湖盆区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物种种类相对单一,但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较大,含有较多的高原特有物种,如雪豹、黑颈鹤等,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高原物种,包括藏野驴、藏原羚、西藏沙蜥等。
“南坡面积较小,河谷深切,坡谷陡峭,相对高差达1000~2000 m以上。雨季时阴雨连绵,具海洋性气候特征。鸟类有雉类、鸠鸽类、鹟类等,东洋界色彩明显。” 科考负责人、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恢复研发中心主任胡慧建说,3300~4000米为古北界和东洋界交会处。
根据地理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分布情况,可将珠峰保护区分为五大片区。分别是喜马拉雅山北坡高原区以及自东向西的陈塘沟峡谷区、吉隆沟峡谷区、绒辖沟峡谷区和樟木沟峡谷区。
“陈塘沟地貌最复杂,它由几条纵横的沟组成,落差大(相对高差达6240米),这条沟里猴子、猕猴、叶猴数量居多。” 胡慧建说,陈塘沟还有不同种类的少见的鼠兔,在这沟里的哑口位置(日屋)有很多雪豹。
雪豹作为珠峰保护区的标志物,可没少调皮。胡慧建说,雪豹常常到村民羊圈偷吃,一般会喝光羊圈所有羊的血,结果就走不动了,就睡觉。当地居民说雪豹喝了羊血会醉,“更可能是它喝血撑到了。”他说,人徒手就可以抓起来,但居民还是会放生雪豹。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潘得巴协会会长次仁罗布也说,雪豹偷吃羊并没有影响村民与动物的关系与情感,村民会大方地放生雪豹,损失由政府埋单。
“还有一个最让我们难忘的是喜马拉雅麝,我们以前没有拍到过,也是很意外地拍到了。”胡慧建说,喜马拉雅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麝其实是一种小鹿。当时,在野外调查时发现,远处有东西,刚开始以为是人,看到在动,马上用长焦镜头拍。他说,这个是很意外的收获,因为喜马拉雅麝特别难出现,它们胆小,特别会躲藏,“在西藏野外还没有拍到过这种麝,以前有人是抓到后拍,我们是野外拍。”
在陈塘沟一带,除了动物,夏尔巴人(指留下来的人)也是主角,他们以“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著称。夏尔巴人是真正的珠峰主人,他们是最会爬山的种族,珠峰的向导几乎被他们垄断。
爬陡坡的羊与马来熊
绒辖沟是四大沟中海拔最高的沟,人迹罕至,是人与动物相处最和谐的区域。
“绒辖沟海拔3000多米,很少有人进去,像天然的野生动物园。” 胡慧建说,绒辖沟内岩羊、藏原羚、熊和叶猴等较为常见,还有喜马拉雅塔尔羊,“这种羊最能爬山。”他说,喜马拉雅塔尔羊爬上80度的陡坡没问题。他强调,绒辖沟有一个特点,“缺乏3000米下的低海拔,蛇和蛙几乎没有。”
时针再往西转,进入到海拔最低的峡谷樟木沟,最低点1433米,到区东部的最高点4369米,水平距离不足20公里,但相对高差达2926米,是罕见的热带、亚热带珍稀濒危物种的集中分布地。
“樟木沟垂直线很多,光照充足,叶猴很多。” 胡慧建说,樟木沟海拔低,最低1440米,热带小鸟很多。
2011年8月,科考队员李晶晶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与5名队友前往珠峰保护区樟木沟进行本底调查,“难抑激动、兴奋之情。”
李晶晶做的是鸟类调查,她说每天都有既定的考察路线和范围,“不蹲点,拍完照片继续前行。”她的初显身手就获得不小斩获,未曾记录的新物种——黑头黄鹂,成为她新增物种名录的一员。
“很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在西藏拍到马来熊。”胡慧建一直认为,马来熊不会出现在西藏。但马来熊也在樟木沟一现身影。起初村民告诉胡慧建团队,沟里有熊,全身是白色和黑色,胡慧建把黑熊照片给当地居民一看,他们说不是,当时他们自然想到熊猫。当地居民透露的另一细节让他们更加欣喜——熊待的地方竹子特别多。“我们很高兴,可能有重大发现。” 胡慧建说,最后证明是马来熊。
当时,李晶晶在边境线做调查,一只大黑熊正移动。她连拍数张照片,事后想起她还有些后怕,马来熊如果过河攻击她,那可不知如何是好。
“拍到马来熊最高兴,它证明了中国亚热带区的动物和热带的动物有交流。对我们影响很大,启发我们多找一些临时性的动物,可能找到很重要的物种。或许还会发现很多热带动物在这存在的证据。” 胡慧建说。
李晶晶说,很多发现都是意外惊喜,他们做的工作是补漏,此前因为条件限制遗漏了很多物种未记录,他们“很幸运”。有一次科考中,司机在路中央发现一条被压死的蛇,带回来一看,原来是稀有物种,以前没有记载。2013年,科考队抓到了活体蛇,记录了更多生物数据,科考队伍给它命名喜山原矛头蝮蛇。
国家新记录棕额啄木鸟
最西面的吉隆沟是最长、最平缓的峡谷,“这是发现物种最多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平坦。”胡慧建说,尼泊尔与中国动物交流主要通过这条沟,全长700多公里,落差3000多米,找动物很好找。他说,岩羊成群,地面可捡到岩羊角。此外,吉隆沟太阳充足,猛禽很多。
蛇也很多,还新发现几种蛙,“因为它很平坦,不像别的地方。水流很急,鱼和蛙就很难生长。”
同样,这些沟谷分布着不同鸟类。2012年,李晶晶在吉隆沟调查时,一头棕额啄木鸟停在朴树上,尾部呈现粉红色,“非常漂亮”。李晶晶赶紧拍照记录,又是一个鸟类名录未收入的物种,成为国家新记录,这对她是一种鼓励。
“看见罕见鸟类,会兴奋几天。”李晶晶说,在可可西里第一次亲眼看到藏羚羊也是异常的兴奋,“与影像当中的感觉很不一样。”
“不同的地形决定不同的物种。”胡慧建总结说,不同的峡谷分布的物种也不相同。
前后历时3年多的本底调查及科考,胡慧建团队收获颇丰,现保护区共记录脊椎动物499种(其中,兽类81种,鸟类390种),占全自治区75%。其中国家Ⅰ级和Ⅱ级保护物种分别为16种和56种。增加新记录兽类9种;鸟类182种;两爬类2种。已鉴定新种1种(喜山原矛头蝮蛇),在鉴定3种,国家新记录1种(棕额啄木鸟)。
胡慧建说,还新发现三种小动物,跟鼠类相似,“有一种现在还没鉴定出来,可以确定是中国新的东西,但是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世界性的新物种。”胡慧建说,另一个问题,标本很少,我们每种都只有一个标本。所以本月中旬将再次考察,找出几个这种动物的标本,以鉴定它们到底是什么物种。
让动物按原本的样子生活
保护野生动物,是本次调查的题中之意也是目的之一。在调查中,保护就已开始。
胡慧建表示,这次调查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最高的地方有一定了解,其次是野生动物其实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资源,动物基因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储备。摸底后知道有什么战略资源可利用。第三,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清楚了,就知道如何保护。再一个,在极端环境,这些动物是如何进化演变过来的,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对动物的研究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些很重要的思想点。在调查过程中,第一,不准带枪,不准猎杀。第二,得到活体,做过测量,拍照后迅速释放……
西藏的神鹰——胡兀鹫、高山兀鹫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一览无余。李晶晶看着它们飞得很自由,有自己的生活规律,“它们在天空翱翔,很壮观。”李晶晶说,他们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记录者,不多打扰兀鹫本来的生活。
胡慧建观察到,当地居民基本上也把动物看做一个生命体,不杀生,这是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如果真的有动物来抓他们的牲畜,他们一般比较宽容。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潘得巴协会会长次仁罗布说,当地居民讲环保,生活方式与环境紧密相连,他举例说,牧民利用牛粪作柴火,环保。同时,他也观察到,相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现在狩猎一个都没有。
次仁罗布是藏区守护者——潘得巴(藏语原意为“为民谋福利的意思)的一员。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潘得巴协会(以下简称潘得巴协会)在当地挑选村民接受环境保护、基本卫生保健和创收等领域的知识技能培训。通过让社区寻找可承受的发展模式以解决环境、健康与经济方面的挑战。1998年被联合国评为“全球五十个最成功的可持续社区发展项目之一”。
次仁罗布说,潘得巴项目采取三方合作模式: 政府领导、外界专家指导、当地居民参与。他说,每个项目当地居民投入50%费用,“为的是减少他们的依赖性,做到可持续发展。”
“我们主要通过给居民培训,教育当地居民保护环境。” 次仁罗布举例说,村民曾大片大片挖掘保护区湿地,用挖出的泥块搭建羊圈。
他说,泥块搭的羊圈,下雨下雪容易坍塌,又需要新挖湿地泥土,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将这些传统羊圈改造成石块羊圈,效果好。改造了70%传统羊圈,保护了高原草甸环境。” 这是协会相当大的成就,次仁罗布同时也意识到,引导村民创收与环保息息相关。潘得巴协会开展了生态旅游项目。
次仁罗布说,协会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厨艺、普通话和礼仪等培训。“这非常重要。”他说,珠峰的旅客猛增,当地村民却吃不上“旅游饭”。他估计,珠峰保护区90%餐厅都是外地人在经营,当地居民没有技能,一般在餐厅服务。
“外地人一般不会从长远考虑珠峰环境,更多的是短期的收益,忠诚度不如当地村民高。”他说当地人是保护区的守护者,应该获得更多旅游红利。
不过,目前生态旅游项目效果不怎样,缺乏支持。但协会从2009年以来,培养了375名“潘得巴”,很大一部分村民更加讲究公共和个人卫生。
胡慧建认为,旅客最重要的是尊重它们的生存权利,尽量保持观赏者角色,不干扰不破坏。第二,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关键,有环境才有动物,进了保护区,带走垃圾,除了留下脚印,不要带走草。人的密度和走动的强度也要注意,大家喜欢到处跑,对植被和动物的干扰大。
《广州日报》(2014-5-13 A7李华)
新闻链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4-05/13/content_2625822.htm#